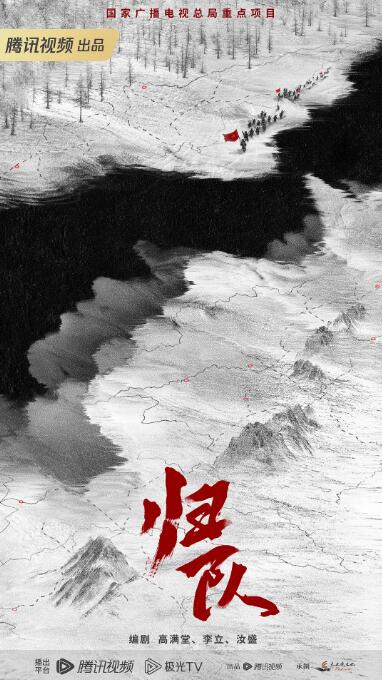-
九州缥缈录
导演:张晓波
上映时间:2019年07月16日
集数:56集
许多年之后,青阳昭武公吕归尘阿苏勒死在他金色的帐篷中。
临死的昭武公等待着家主和学士们商议他的谥号。他握着大合萨颜静龙的手说:“我曾经立誓要守护青阳和我所爱的人们,可是我错了。我太自大了啊!其实我的能力,只能守护那么区区的几个人而已。可惜他们,都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了
临死的昭武公等待着家主和学士们商议他的谥号。他握着大合萨颜静龙的手说:“我曾经立誓要守护青阳和我所爱的人们,可是我错了。我太自大了啊!其实我的能力,只能守护那么区区的几个人而已。可惜他们,都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了
那些男人聚在一起
他们可以颠覆天下
翼天瞻老师陷入回忆时出神的说
他们可以颠覆天下
翼天瞻老师陷入回忆时出神的说
临死的昭武公等待着家主和学士们商议他的谥号。他握着大合萨颜静龙的手说:“我曾经立誓要守护青阳和我所爱的人们,可是我错了。我太自大了啊!其实我的能力,只能守护那么区区的几个人而已。可惜他们,都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了。”
“那年我在清平原遭遇威武王,败在他的刀下,”姬野总是说,“后来我赢得了天下”
方都尉,要是你最亲的人都听不到你的消息了,当英雄还有什么意思呢?”
"真的不杀他?"谢玄策马贴近嬴无翳的身边。
嬴无翳摇头:"等将来吧。"
"只怕会是将来的灾祸吧?"谢玄感喟一声,并不再劝。
"天驱的小孩,你叫什么名字?"嬴无翳忽然拉住战马,回身喝问。
"姬野,荒野的野。"
"荒野的野……好!有朝一日若是成为名将,"嬴无翳大笑,"就来和我争夺天下!"
嬴无翳摇头:"等将来吧。"
"只怕会是将来的灾祸吧?"谢玄感喟一声,并不再劝。
"天驱的小孩,你叫什么名字?"嬴无翳忽然拉住战马,回身喝问。
"姬野,荒野的野。"
"荒野的野……好!有朝一日若是成为名将,"嬴无翳大笑,"就来和我争夺天下!"
然后他昏了过去,等到家主们把议定的“昭武”谥号传进金帐,他才又一次睁开眼睛,说了一句历史上无人能解的话。
再然后他就死了。
颜静龙平生第一次觉得手中的手掌松开了,垂垂老矣的大合萨忽然忍不住放声大哭,想到许多年前炽烈的阳光下的那个孩子。
“我会保护你的。”其实他的一生只是为了这句话而活着。
再然后他就死了。
颜静龙平生第一次觉得手中的手掌松开了,垂垂老矣的大合萨忽然忍不住放声大哭,想到许多年前炽烈的阳光下的那个孩子。
“我会保护你的。”其实他的一生只是为了这句话而活着。
那也是青阳昭武公的一生中,唯一一次拥抱这个他等待一生的女人。那时候他觉得莫大的悲伤和莫大的幸福一起到来,却不知道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大概神恰巧无聊,怜悯他的等待,在冥冥中以一根手指沾了些许蜜糖抹在他的唇上,之后神又遗忘了他,于是青阳昭武公只能在落日时独坐在他的金帐中,凭着记忆回味那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微甜。
高天上的武神俯视大地,背负着他意志的少年们将尚且稚嫩的手掌放在了一处,
乱世的君王们就此结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盟誓。
有一种意志不随时光磨灭,
有一种火焰总要焚烧荒野。
可曾听见天空外的鹰在长唳?
可曾听见大地下沉重的呼吸?
新的时代,已经解开了序幕。
乱世的君王们就此结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盟誓。
有一种意志不随时光磨灭,
有一种火焰总要焚烧荒野。
可曾听见天空外的鹰在长唳?
可曾听见大地下沉重的呼吸?
新的时代,已经解开了序幕。
息衍转过去看着女人,他只要穿过那片火海就能把她拉出来,他不怕火焰,也不怕崩塌的大殿,可是他觉得女人离他很远,远得一辈子都无法触到她的手。
“他跪在大君面前接下了那个孩子,他说:‘那就由我为他起名,我叫他'阿苏勒!'”
“阿苏勒,意思是长生。”
“阿苏勒,意思是长生。”
想用那枪?就用血魂去换,换得干干净净,九州大地上就再无人是你的对手!
他骑着小马,沿着彤云大山的山脚,慢慢的走向南方。青阳的豹云旗和下唐的金色菊旗帜在他的头顶招展,有如大海的波涛。
青铜家族的孩子,你以生命侍奉苍青的君主,被赐予荣誉和长生。
冷风灌了进来,掌柜上去关了窗子。 窗子关上了,吕归尘再也听不见什么。
他站在巷子里,背靠着墙,里面是他最好的朋友和注定要毁掉他一生安宁的女孩。
他想如果他不认识羽然就好了,最好也不认识姬野。这样他是南淮城里的一个小蛮子,他穿着蛮族式样的大袖,胸前骄傲地配着他的小佩刀,虽然人人都看不上他。他虽然也会在秋风来的时候看着从北方来的大雁,想着他的父亲、母亲、苏玛和大合萨,不由得伤心,可是他不会像现在这么难受,这种难受是淤积在他心里的,让他很想大口地呼吸,把一切都呼出去。可是没有用,他的心里被粘稠的难受填满了,没有一点儿空隙。
他站在巷子里,背靠着墙,里面是他最好的朋友和注定要毁掉他一生安宁的女孩。
他想如果他不认识羽然就好了,最好也不认识姬野。这样他是南淮城里的一个小蛮子,他穿着蛮族式样的大袖,胸前骄傲地配着他的小佩刀,虽然人人都看不上他。他虽然也会在秋风来的时候看着从北方来的大雁,想着他的父亲、母亲、苏玛和大合萨,不由得伤心,可是他不会像现在这么难受,这种难受是淤积在他心里的,让他很想大口地呼吸,把一切都呼出去。可是没有用,他的心里被粘稠的难受填满了,没有一点儿空隙。
要还是当年的我,舍了命也要保伯鲁哈,把那些人一个一个都杀了,又算得了什么?骑着马跑在草原上,多少人来打我,我又怕过什么?可是我不能了,我是草原的大君。
“姆妈,不要离开我,”孩子喃喃地说,“我会……保护你啊!”
阿苏勒,我们喝酒去。
“天生古月衣!”
姆妈,不要离开我,我会……保护你的。 ——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
北辰之神,穹隆之帝,万宗之主,无始无终。
他直起身,漫天雪花中,忽然一抖大袖,大笑,临风起舞,仿佛粉墨登场的戏子,“我有屠龙之术,欲翻云龙起舞;我有沧海之志,欲煎七海成田;我怀绝世之锋,欲解抵天之柱;我是藏玉之璞,欲觅神匠成材!”
可是世间却没有一个戏子有他的猖狂和才具。
他收了舞姿收了笑容,蹲下身低头看着叶雍容,神色认真,“我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世间却没有一个戏子有他的猖狂和才具。
他收了舞姿收了笑容,蹲下身低头看着叶雍容,神色认真,“我说的,都是真的。”
当这个世界都要崩溃
当星辰和阳光也熄灭
当马蹄踏过弱者的尸骨
当黑暗的血色吞噬人心
英雄还在哭泣
在铁铸的摇篮中成长.......
当星辰和阳光也熄灭
当马蹄踏过弱者的尸骨
当黑暗的血色吞噬人心
英雄还在哭泣
在铁铸的摇篮中成长.......
阿苏勒,我来救你了
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没用的人。 ——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
她脸上还带着泪水,可是已经没有了表情,那么安静,静得让他心颤,像是已经死去的荒凉。
不要揣测神的心,我的孩子,”老头子的声音仿佛梦呓,“神的胸膛里没有心,那只是一块铁石
阿苏勒忽然明白了,当他们在地宫里背靠墙壁仰望头顶的黑暗时,钦达翰王为什么要向他讲述盘鞑天神的神话。这个老人分了许多次,把那个浩瀚而血腥的神话拆开来,灌入他的脑海。这和白毅把他处世的经验用呆板教条的方式灌入小舟公主的脑海一样,因为相处的时间太短暂,要你记住这些,将来会有用,将来你忽然领悟了童年时那些教导中蕴含的深意时,你才明白教你的那个人是多么爱你。而等你明白的时候,你们已经远隔天涯或者生死。别人的爷爷可以和孙子一起吃饭、一起逗趣、一起骑马、一起射箭,在漫长的时间里传递积累了几十年的知识,直到他爷爷老了,死在床上。可他的爷爷不行,钦达翰王没有时间,他只能用神话把一切浓缩起来,呵斥阿苏勒,要他铭记在心。他在讲述那个神话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计算分别
羽然……为什么有的人会喜欢一个人,可是别的人却都不喜欢他呢?”
羽然想了想,“我不知道啊,不过爷爷说过,人的心里都是很小的,容不下好多东西,你只能喜欢那么几个人,最喜欢的也许只有一个人,那么你的心思都花在他身上啦,就没法喜欢别的人啦。”
羽然想了想,“我不知道啊,不过爷爷说过,人的心里都是很小的,容不下好多东西,你只能喜欢那么几个人,最喜欢的也许只有一个人,那么你的心思都花在他身上啦,就没法喜欢别的人啦。”
后世的史家们谈起这次南行,总是带着疑惑和赞叹的语气。
他们总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一只绵羊被放出了羊圈,他就变成了咆哮的雄狮,怒吼着奔向了东陆大地。无论是英雄或者救主,无人可以否认,点燃乱世战火的手中,有一只是属于青阳昭武公吕归尘的。他的理想他的志向最终化为焚烧世界的烈焰。他骑着火红的战马要去拯救这片天下,却发现自己的马蹄下踩满了弱者的尸骨。
他们总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一只绵羊被放出了羊圈,他就变成了咆哮的雄狮,怒吼着奔向了东陆大地。无论是英雄或者救主,无人可以否认,点燃乱世战火的手中,有一只是属于青阳昭武公吕归尘的。他的理想他的志向最终化为焚烧世界的烈焰。他骑着火红的战马要去拯救这片天下,却发现自己的马蹄下踩满了弱者的尸骨。
“不要过来!”他用尽全力把青鲨横在公主的脖子上,“不要过来!”
“你已经战败!”嬴无翳勃然大怒,“难道天驱的武士,就是这样的贪生怕死?不知羞耻?”
“羞耻?”姬野的面孔扭曲,“你们那么多人……都要杀我。你们所有人!羞耻……什么叫贪生怕死?每个人都要活下去的!为什么说我贪生怕死?我要活着回去!我要是死了,谁也不会管我,谁也不会管我的!”
“你已经战败!”嬴无翳勃然大怒,“难道天驱的武士,就是这样的贪生怕死?不知羞耻?”
“羞耻?”姬野的面孔扭曲,“你们那么多人……都要杀我。你们所有人!羞耻……什么叫贪生怕死?每个人都要活下去的!为什么说我贪生怕死?我要活着回去!我要是死了,谁也不会管我,谁也不会管我的!”
我曾想就算用自己的脸去挡,也不让人再踩他的脸。他擦了擦脸上的血说,没必要,踩我脸的人,我都会一一杀掉。我总是怀疑这个人其实没那么狠,他只是个孤独的小孩,那些他曾誓言杀掉的人,还都好好地活着,在他的庇护下,甚至觊觎他的宝座。很多年前我鼓起勇气准备去死的时候,这家伙发疯一样背着十二把刀来救我,他像疯子一样见人就杀,披着血,冲向我,高喊说,阿苏勒,我来救你了。别说我蠢,姬野,你没蠢过么?
南淮还是不是那个南淮都已无所谓,可是和你偷花跳板打枣子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因为巴莫鲁叔叔说诃伦帖姆妈将来嫁人了,就不能做我的姆妈了,她要去跟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养她自己的孩子,所以,”吕归尘看着自己的脚尖,不好意思地蹭着地面,“我想要是我娶了姆妈,姆妈就可以一生都跟我在一起了。”
女人又笑,吕归尘觉得从未在她脸上看过那么多笑。
“后来呢?”女人拉着他的手,“你什么时候明白过来的?”
“后来……后来姆妈死啦,”吕归尘的神色黯然下去,“永远都不能跟我在一起了……”
女人又笑,吕归尘觉得从未在她脸上看过那么多笑。
“后来呢?”女人拉着他的手,“你什么时候明白过来的?”
“后来……后来姆妈死啦,”吕归尘的神色黯然下去,“永远都不能跟我在一起了……”
北辰之神,风履火驷;其驾临兮,光绝日月!
“将来我长大了就能飞得更远,带你一直飞到宁州去看森林,我们去找龙也不用造船了,我带着你飞过去!”
大概神恰巧无聊,怜悯他的等待,在冥冥中以一根手指沾了些许蜜糖抹在他的唇上,之后神又遗忘了他。
东陆什么都有,可是偏偏没有他想要的。
你还想保护别人?你能么?你能么?你现在在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你连自己都救不了!
“息衍,你真的能以天下人为猪狗?” “不是我以天下人为猪狗,”息衍低吼,“我就是猪狗!” “你!”白毅也怒极,言语却涩住了。 “这茫茫天下,有几人知道我们的梦想和苦难?”息衍的声音干涩,透着无尽的悲凉
为了融入人群他们愿意感受肉体的苦痛,但在人群中他们始终又是孤独的异类。
《燮河汉书·项空月列传》中提到羽烈王征讨陈国,兵临城下,陈国大将费安力劝国主不降,双方僵持三月,最后羽烈王击破陈军本阵,阵斩费安,生擒陈国公。以羽烈王行军的惯例,不降而破的城池,百夫长以上一律就地处死。陈国公不降,也难逃一死。但是陈国公年幼,又精通琴艺,太傅项空月怜惜他的才华,想救他一命,于是给了他一幅画,让他在面见羽烈王的时候把画献上。
陈国公精通书画,看那幅画不过是街头画匠的手法,毫无章法意境,不禁也怀疑。但是项太傅劝他不必担心,只说这幅画是当初下唐南淮一个流浪的画师无意中在街头捕捉真人的背影画下的,天下纵然广大,这幅画却是不可再得,一定可以救得陈国公一命。
陈国公听从了项太傅的话,当廷献上画作,最后果
陈国公精通书画,看那幅画不过是街头画匠的手法,毫无章法意境,不禁也怀疑。但是项太傅劝他不必担心,只说这幅画是当初下唐南淮一个流浪的画师无意中在街头捕捉真人的背影画下的,天下纵然广大,这幅画却是不可再得,一定可以救得陈国公一命。
陈国公听从了项太傅的话,当廷献上画作,最后果
紫槐花开放的季节,让我说爱,
爱飞翔的蒲公英都要走了,让我们唱歌,
那些唱歌的松树都结籽了,让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让我们说爱,让我们唱歌,让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爱飞翔的蒲公英都要走了,让我们唱歌,
那些唱歌的松树都结籽了,让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让我们说爱,让我们唱歌,让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我想过要是我是青阳的大君该多好,只要我说不打了,大家就都不打了。
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够了!够了!你现在说了又有什么用?你不是青阳的大君,你只是个小孩子,你能做什么?你们青阳的铁骑现在就在战场上杀我们真颜部的人!你能救得了谁?
不要再说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诃伦帖
不要再说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诃伦帖
白水淘尽沙,
丫头鬓发白。
浣纱人归晚,
同舟共采莲。
丫头鬓发白。
浣纱人归晚,
同舟共采莲。
我该拿你怎么办?怎么办!
直到大燮神武六年,羽烈王高坐在太清阁的临风处宴饮,对“燮初八柱国”之一的谢太傅说了这段往事。
帝王端着杯盏眺望远处:“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知道这个茫茫的世界上,竟然可以有什么东西只属于我,而不属于昌夜。那一夜我都没有睡着,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下了决心。我不要做弟弟的副将,我要做自己的事。如果羽然会和我站在一起,那么漫天诸神也未必都只眷顾昌夜,我要这天下属于我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再也不要追随在别人的马后。我再也不要,追随在别人马后!”
太傅沉吟良久,苦笑着说:“这话可以流传下去么?”
帝王微笑:“太傅怎么想?”
太傅思索了良久:“八字而已。可敬可畏,可憎可怖。”
帝王端着杯盏眺望远处:“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知道这个茫茫的世界上,竟然可以有什么东西只属于我,而不属于昌夜。那一夜我都没有睡着,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下了决心。我不要做弟弟的副将,我要做自己的事。如果羽然会和我站在一起,那么漫天诸神也未必都只眷顾昌夜,我要这天下属于我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再也不要追随在别人的马后。我再也不要,追随在别人马后!”
太傅沉吟良久,苦笑着说:“这话可以流传下去么?”
帝王微笑:“太傅怎么想?”
太傅思索了良久:“八字而已。可敬可畏,可憎可怖。”
神不救任何人的灵魂,它只是创造,和毁灭。
我的孩子,大神的威光与你同在,你的魂将不朽,永远行走在天空上,与星辰同命。
他忽然觉得老人很可怜,跟自己一样可怜,全天下的人都那么可怜,可他只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力量。
一个人活的越久,往往越不坚定。
忽然发现天地很大,自己懂得很少,不懂是的难道不是孩子么?
他从小就怪怪的,一点都不懂事,我是来杀他的,他还跟我讲过去的友谊……很多年前我带着十二柄长刀去劫法场救他,因为那时他是我在这世上最好的朋友,我的朋友总是很少,失去他,我会很孤独。如今我已经坐拥天下,无数人愿意为我去死。我不必害怕失去任何人。我们曾定约说,要活过乱世,共有天下,他在北边,我在南边,每年开春冰化的时候,他坐着船,渡海而来,和我饮酒。而今我们已经分享这天下了,他渡海而来,带着刀剑铁骑。我已经没有朋友了,皇帝不需要朋友。
义是行商蠹,仁是领军蠹,情是人心蠹。
“不知道能否用金钱换回尸骨,”谢玄低低叹了口气,“苏元朗是王爷旧部,我们所剩不多的最初的战友,如果尸体都不能收葬家乡……”
“不必了,”嬴无翳挥了挥手,“有朝一日我取下东陆,哪里都是离国!哪里都是家乡!葬不葬在离国又有什么分别?”
“不必了,”嬴无翳挥了挥手,“有朝一日我取下东陆,哪里都是离国!哪里都是家乡!葬不葬在离国又有什么分别?”
“君为昌夜,自苦若此。此诚父爱,宁不惜我。”
“你为了昌夜那么自苦,这诚然是父爱,可是你就不怜惜我么?”此刻燮羽烈王的声音里也透出了一股源自少年时的辛酸孤独,却也见得他对自己的父亲还是抱着某种隐藏很深的期待了。
“你为了昌夜那么自苦,这诚然是父爱,可是你就不怜惜我么?”此刻燮羽烈王的声音里也透出了一股源自少年时的辛酸孤独,却也见得他对自己的父亲还是抱着某种隐藏很深的期待了。
“真傻……”他轻声说。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谁,也许是说自己,也许是说羽然,说那么多隐隐约约的眷恋和表白你始终都不明白,只是在下午的阳光里雀跃着爬上树去摇晃挂满枣子的树枝。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谁,也许是说自己,也许是说羽然,说那么多隐隐约约的眷恋和表白你始终都不明白,只是在下午的阳光里雀跃着爬上树去摇晃挂满枣子的树枝。
没有平静的世界,神创造这世界,就是使它为战场。
神所庇佑的人,他不可阻挡。神授予他武神般的力量,狮子般的雄心,火焰般的渴望,钢铁般的意志。一切的敌人都将在他的面前化为齑粉,仿佛遭到雷霆的惩罚!神的眼睛在天空里俯视他,奇迹跟随他而行。神曾为了拯救河络一族而劈开大山,也会为了他所选中的人把殇阳关变成白毅的森罗地狱!即便是军王,也不足以抗衡神的意志!
我喝着酒,想起我第一次遇见大燮的皇帝,那是月光下一只受伤的幼虎,或者一个孩子。“我……我叫吕归尘,吕归尘·阿苏勒,你可以叫我阿苏勒。”“我叫姬野……荒野的野。”
在命运的轮转中,那叫阿苏勒和姬野的孩子都死了,只剩下大燮的皇帝和蛮族的君王。
——青阳昭武公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
在命运的轮转中,那叫阿苏勒和姬野的孩子都死了,只剩下大燮的皇帝和蛮族的君王。
——青阳昭武公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
我们是武神的使者,是北辰指引下的武士,我们因尊严而荣耀,因勇敢而自豪,我们坚定的信仰一如森然铁甲,守护着脆弱人世,守护着无数善良而柔弱的魂灵,我们的血从不白流,我们的奉献无始无休!
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见到大燮的皇帝,此后我们中无论谁,都恪守诺言,不再踏上对方的土地。每年春天,我骑著战马去草原的南方,在海峡边饮酒、眺望,可是天拓海峡那么宽广,即使羽人的视力也看不到对岸。我喝著酒,想起我第一次遇见大燮的皇帝,那是月光下一只受伤的幼虎,或者一个孩子。
“我……我叫吕归尘,吕归尘·阿苏勒,你可以叫我阿苏勒。”“我叫姬野……荒野的野。”在命运的轮转中,那叫阿苏勒和姬野的孩子都死了,只剩下大燮的皇帝和蛮族的君王。
“我……我叫吕归尘,吕归尘·阿苏勒,你可以叫我阿苏勒。”“我叫姬野……荒野的野。”在命运的轮转中,那叫阿苏勒和姬野的孩子都死了,只剩下大燮的皇帝和蛮族的君王。
我不见万古英雄曾拔剑,铁笛高歌龙夜吟;
我不见千载胭脂泪色绯,刺得龙血画眉红。
我不见千载胭脂泪色绯,刺得龙血画眉红。
这是吕归尘记忆中羽然唯一一次抱他,他个头比羽然高,可是这个时候却是羽然在抱他。羽然身上淡淡的香气笼罩着他,他觉得羽然的身体是那么软,软得可以融化到他的身体里面,他又觉得其实那是因为他自己变得太柔软了,羽然用力一捏,他就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人儿,可以放在羽然的口袋里,跟着羽然去很远的地方。
战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要喝酒,想起他们跟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 ——谢圭
“但是男儿生在世间,有很多不得以的事,”雷千叶说,“恩情和男儿的伟业,是无关的。”
“不管南淮还是不是那个南淮,当年那个和你偷花打枣跳板子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啊。”
悲喜总无泪也,是人间白发,剑胆成灰。
“在这乱世之中,跟砍下离国公嬴无翳的人头比起来,其他的,都算不得功名。”息衍对姬野说。
越千山
过大江,
绝天海,
与子征战路漫长。
收我白骨瀛海旁,
挽我旧弓射天狼。
过大江,
绝天海,
与子征战路漫长。
收我白骨瀛海旁,
挽我旧弓射天狼。
夫万载之远,天地之分,无九州七海之谓,世间诸族,本骨肉之无间,交相亲爱,同涉沧桑。
百代之遥,神帝立国,无三陆华夷之隔,普天万民,皆兄弟之共融,平安谐乐,共辅英主。
天下何以裂分,兄弟何以征战,人心何以背离,东陆北陆血肉之亲,何以竟成寇仇。吾每思及此,常自扼腕。
百代之遥,神帝立国,无三陆华夷之隔,普天万民,皆兄弟之共融,平安谐乐,共辅英主。
天下何以裂分,兄弟何以征战,人心何以背离,东陆北陆血肉之亲,何以竟成寇仇。吾每思及此,常自扼腕。
我们是世界的主人。我们掌握的力量是凡俗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我们可以使死人活过来,更可以使活人死去;我们可以使大地开裂,也可以使雪山融化;我们可以唤来太阳一样的光明,也可以让世界永远沦入黑夜。
就是在那天夜里,神卜池中的玄明全身赤红而死,祖庙地宫中的万年灯熄灭,彤云大山的山顶泛出金色的光芒,三颗并排的大流星穿过北都城的天野,天空明亮如白昼。一切都和《石鼓卷》的预言相同,那是天神对世人的惩罚,草原变成血红的颜色,变成满是死人的地域。不过,蛮族迎来新的时代,英雄拔出火山中的神剑,跨着狮子头的雄鹰统一草原,盘鞑天神拥有了天空,把大地和海洋留给他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铁沁王,山与海之王!
“喝啊!喝啊!喝啊!”这支沉寂的军队忽然爆发出巨雷一样的呼喊。有一种精神点燃了他们每个人的意志,他们高举起武器直指天空,数百人的吼声将整个荒原上敌军的声浪压了下去。
“只要最后一个天驱还活着,总有人镇压他们的野心!”首领仰天吼叫,“铁甲……”
“依然在!”所有人都随着他咆哮。
“铁甲!”
“依然在!”
“铁甲!”
“依然在!”
三次一次更比一次沉雄的吼声震惊了整个荒原,仿佛巨龙呼啸着从夜雨中升腾而去,狂烈的龙吟化作沉重的雷声在整个荒原上滚动着推向四周。天空中的云层也震颤着要为之崩溃。发动冲锋的敌军在这阵不可一世的咆哮声中敬畏不安
“只要最后一个天驱还活着,总有人镇压他们的野心!”首领仰天吼叫,“铁甲……”
“依然在!”所有人都随着他咆哮。
“铁甲!”
“依然在!”
“铁甲!”
“依然在!”
三次一次更比一次沉雄的吼声震惊了整个荒原,仿佛巨龙呼啸着从夜雨中升腾而去,狂烈的龙吟化作沉重的雷声在整个荒原上滚动着推向四周。天空中的云层也震颤着要为之崩溃。发动冲锋的敌军在这阵不可一世的咆哮声中敬畏不安
你有十二分的才华,可是只有八分的耐心,出来的也只有八分成就。
“有一件事我想问你……”白苌忽然对姬野说,“你觉得未来是能被改变的么?““能,假如改变本身即是未来的一部分的话。”“是么……”白苌轻声说。
『他提着沉重的铁弓,腰间捆满箭囊,马鞍上捆着明晃晃的十二柄长刀。那真的是一只刺猬,一只愤怒的刺猬,它的目光漆黑得像是雷电。「阿苏勒,我来救你了。」姬野说。
人生就是这种捣鬼的东西,你汲汲于名利的时候,名利远在天边你想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又听大明宫中传你作诗
没有人会知道,因为他总是低着头,所以无人看见他眼底的孤独。
知道得太多,还不如蒙昧。
人生苦短,兵者不祥,积尸百万,无非子民,为王者,纵于九幽下身受斧钺之刑,心能安乎?
不同的人,血管里流着相似的血,所以他们终究走到一处
“我只是忽然觉得我对你的背影那么熟悉。仔细回想,每次我们有约都是我去看你的背影,”息衍摇着头,笑了笑,“所以我想看一看你回头。”
孩子也在哆嗦,他转过头去对着虎豹骑战士们的马刀,慢慢地张开了双臂。那件月白色袍子的两袖像是小鹰的双翅,谁都明白他是要做什么了——他把龙格凝挡在自己的身后。
不要揣测神的心,我的孩子,神的胸膛里没有心,那只是一块铁石。
极天之高,极地之远,皇帝之信,威临九州。
圣人者,于万难之际,守衷不改,不以褒贬而易志,不以得失而悲喜,不以成败而俯仰,此俗子所不能。夫天地之大,道贵一也,圣人得其理,是谓圣也。
所谓英雄,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不冒绝大的危险,又怎么能成就大事?一个人宁愿成为英雄而死,也不愿当一个懦夫而生。
或许是不知梦的缘故,流离之人追逐幻影。
羯鼓声里沥新酒,酒暖读入喉
羯鼓声里沥新酒,酒暖读入喉
在战场上,你总要相信些什么人,那是你的勇气,令你陷入绝境仍能挥刀死战。
大燮神武年间华族与蛮族相隔天拓海峡对峙,彼此为仇敌。夑皇【姬野】(夑羽烈王)邀约蛮族大君【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青阳昭武公)会于唐兀山口,谈判停战。
再次见到那个男人时,我已经忘了我们之间的诺言;我曾许诺用生命保护他,而今我要杀了他;因为他是蛮族人的君王,而我是华族的皇帝。
这世上很少人能懂皇帝,因为他们不曾坐在这个孤独的座位上;你拥有天下而又被世人献祭于神;你须杀死一切的敌人,否则你便被他们杀死。
——夑羽烈王·姬野
他老了,忘记了怎么笑;他累了,那双熟悉的黑瞳里没了温暖;他曾经立志不再跟在别人的马后奔驰,如今他已是天下的头马。在他还是个孤独奔跑的孩子时,他是我的朋友,他叫姬野;在他带甲十万人、冠盖满天下时
再次见到那个男人时,我已经忘了我们之间的诺言;我曾许诺用生命保护他,而今我要杀了他;因为他是蛮族人的君王,而我是华族的皇帝。
这世上很少人能懂皇帝,因为他们不曾坐在这个孤独的座位上;你拥有天下而又被世人献祭于神;你须杀死一切的敌人,否则你便被他们杀死。
——夑羽烈王·姬野
他老了,忘记了怎么笑;他累了,那双熟悉的黑瞳里没了温暖;他曾经立志不再跟在别人的马后奔驰,如今他已是天下的头马。在他还是个孤独奔跑的孩子时,他是我的朋友,他叫姬野;在他带甲十万人、冠盖满天下时
息衍低声回应,“臣的老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勇气。大战在即,脸红是血勇,脸白是骨勇,脸青是气勇……不过这些都还不算真正的勇敢。”
“那姬野又如何?”国主喝问。
“面色不变,拔剑生死,”息衍沉声道,“当然是神勇!”
国主哑然
“那姬野又如何?”国主喝问。
“面色不变,拔剑生死,”息衍沉声道,“当然是神勇!”
国主哑然
何当重整风炎血,再起龙旗向阿山!
北辰之神,明昭大荒,允文允武,无竟维烈
千里彤云山,并跨日与月。
天女倾银瓶,流出雪嵩河。
神山做天柱,雪河饮神马。
骏蹄飞踏处,寸寸碧草生。
山神啸云间,常闻虎豹声。
男儿生来铁筋骨,跨我骏马兮,向远方。
天河水如乳,育我万千人。
女儿生来唇抹朱,牧我银羊兮,守故乡。
天女倾银瓶,流出雪嵩河。
神山做天柱,雪河饮神马。
骏蹄飞踏处,寸寸碧草生。
山神啸云间,常闻虎豹声。
男儿生来铁筋骨,跨我骏马兮,向远方。
天河水如乳,育我万千人。
女儿生来唇抹朱,牧我银羊兮,守故乡。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知道这个茫茫的世界上,竟然可以有什么东西只属于我,而不属于昌夜。那一夜我都没有睡着,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下了决心。我不要做弟弟的副将,我要做自己的事。如果羽然会和我站在一起,那么漫天诸神也未必都只眷顾昌夜,我要这天下属于我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再也不要追随在别人的马后。我再也不要,追随在别人马后!
皇帝抬起头,看着那匹烈火般的红马奔驰着越过草原,登上山坡,在最颠峰处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嘶,而后永远离开了他的视线。自始至终,蛮族武士不曾回头。
在南淮城多雨的秋天里,老人揭开丝绵,端详着古老的巨剑。剑里那些不能解脱的魂魄还在咆哮,真正的腥风血雨,已经在东陆的天空上卷起了墨黑的阵云。
战争序幕于鲜血尚未凝固前的再次拉开。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时刻,谷玄和北辰在星空中看不见的角落,以满潮之相对冲……
吕归尘会拼命地去回想他和羽然在一起的一点一滴,他怕遗忘,他想是否曾有那么一刻,羽然的心里对他有过那么一丝异样的情怀。可是他不知道。于是他仅仅能一再地回忆他的手指划过羽然的长发时,仿佛划过纤细如丝的时光。他揽不住时间,只能在风一般的触感里面去见证曾经有过的一切。
战,唯死,不降。
麻木尔杜斯戈里亚,猛虎之牙,撕裂卑怯者的灵魂。
如果敌人不择手段,那你的仁慈只是一种怯懦!
生死之间,存亡之夕,此人生不可不断之时。圣人者,不惊,不惧,不急,不缓,乃胸中自有丘山,步深渊如行广道,纵油鼎在前刀剑在侧,亦信步越之。
杀人,上将以谋,中将以策,下将以战。
“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但是,我不想再这么没用了!”
圣人能救我么?圣人上过战场么?要是上过,他早就被杀掉了。
这个世上本来就是最血腥最残忍的,英雄们都是杀人的魔鬼,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你握着刀,变成了魔鬼,杀了你的敌人们,你才能保全你的家族和你心爱的人。
“蔷薇公主想的是当她帮着蔷薇皇帝当上了皇帝,她就会带着文纯公子的骨灰回乡下。” “再后来呢?”“后来她就死啦,没能看见蔷薇皇帝登上皇位。”“再后来,他也死了,虽然登上了皇位,可是没有娶到蔷薇公主。”
二十年前,我和息衍还是朋友,都汲汲无名,曾想过在帝都的街头开店卖花,赚一点钱花销。那时候息衍还说开店便要有绝活,别人没有的,才能红火起来,于是他研究了一个夏天,种出一色蓝边的玫瑰,称为海姬蓝。
“我把这柄刀送给你,以后有谁敢踩你的脸,也就是我阿苏勒·帕苏尔的敌人,这个誓言只要我不死,就都有效!”
“天驱……你们这样的人,有很多么?”
“有过很多,但是都死了。”
“有过很多,但是都死了。”
其实每个人活下去都要很多的勇气。
那是点燃了一个时代的目光,是刀剑,是枪戟,纵然折断也不屈悔。
“我叫吕归尘,吕归尘·阿苏勒,你可以叫我阿苏勒。”“我叫姬野……荒野的野。”
我遇王,而知天下偌大。
吕归尘一生中过去的十七年里,从没有任何时候像这一瞬。这一瞬吕归尘想活下去,想要看见明天早晨的阳光,看见晨光中他的朋友们,看见金色的长发在风中飘洒如光缕。
“我会保护你的。”其实他的一生只是为了这句话而活着。
北辰之神,浩瀚之主,泛乎苍溟,以极其游
臣能活多久?可是史官代代,下笔如刻金铁,不漏言,不妄语,世代家风,不能毁在臣手里。
北辰之神,苍青之君,广兮长空,以翱以翔
英雄们即将相遇,武神铁青色的手在冥冥中拨转他们的方向。沉默已久的乱世之轮重新开始运转了,它擦着耀眼的火花,把灾难和泪水、火与水,一同抛向了九州大地。
“铁甲依然在!”“依然在!”
“依马德,古拉尔,纳戈尔轰加,这是我祖宗的血!他们的灵魂在黑暗中看我,他们传给我尊贵的血和肉,他们传给我天神的祝福!我们注定是草原之主,我们注定是世界的皇帝,我们注定是神唯一的使者!”
那一夜,南淮城的星空下,她以她的天真无邪点燃了一颗燃尽天下的火种,在他最孤独的时候。
“可是你手中有枪,这是一杆古老的枪,你的曾祖拿着它的时候,任何和他对面的人都心惊胆战。谁敢看不起他?你要做空前绝后的武士,那么不是战一人,而是战天下!”
“羽然,我该拿你怎么办?”他喃喃的说,看着笔尖的墨水滴落在白色的罗绢上,晕出一个个墨点,“我该拿你……怎么办?”
许多年后吕归尘膝上放着一个女孩,坐在腾诃阿草原的天幕下,他对女孩说人一生便是如此,你要找一个归所,可是天地便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你不知道哪一次该转弯哪一次不该,也许你奋力前进,却离自己想去的地方越来越远。
北辰之神,凭临绝境,唯心不动,万垒之极
要知道你为什么出枪,你的心里有闷烧的火,那是大地上燃烧的煤矿,它的火焰终有一天烧破地面去点燃天空。你会吼叫,因为你若是不吐出那火焰,它会烧穿你的胸膛,它像是愤怒,又像是高亢的歌,龙虎的吼声让时间停止。
“既然你们真要把这天下变成苍生的战场,那么我向你们宣战,不死不休!”
青阳昭武公回想他一生中最温软的时光,是在南淮城的街头,他和他心爱的女孩儿并着肩走,有时候羽然也会拉住他的手,而有的时候她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高声呼喊让他走快一些,曾经在那些深寂的小巷里,她没来由地唱歌,这时吕归尘总是以为他是在做一个很漫长的梦,长到不会再醒来。
“要相信老人的话,我们可不是那些矫情的年轻人,说着谎话劝别人离开,自己留下来独自战死。”…苍溟之鹰 翼天瞻
“谁敢用一个心比天高的小卒?”“谁又甘心永远只是一个小卒?”
男人长大了,最好的朋友便只剩下刀剑。
“如果我拥有九州,我会把一州送给你,表示我的感谢,可惜我连立足的土地都没有。如果我富甲天下,我会给你一生用不尽的金银,可惜我只是一个流亡兵团的首领,我甚至没有钱给我的战士们买盔甲和战马。我所能做的只是让你开心一下,就算我的回报吧……你开心么?”姬野
北辰之神,穹隆之帝,其熠其煌,无始无终
我昭武的理想,已经在七年前的火雷原上,都结束了。---吕归尘
水畔听钟七十年,便了却了此生。
庙堂既高,箫鼓老也,烛泪堆红,几人歌吹
北辰之神的光辉照在我们彼此的双肩,我们因尊严而自豪,因勇敢而骄傲。铁甲依然在。
一件东西,如果已经不堪守护了,不如摧毁它,重新来过。
“翌年春,稷宫的梨花再次盛开,洁白如雪,可是曾在梨花树下席地而坐纵酒唱和的年轻人们都已经离去,风炎的英雄血脉如燃烧之后的残灰般飞散在历史的书页间,墨迹中徒留下写不尽的英雄志、唱不尽的男儿气、望不到头的漫漫征途。”
所有武术,追究到最初都只是一种杀人的手段。 这血的事实,不容改变,也无需被改变。
更多台词
最近热播剧 最近综艺节目 最近上映电影
地球超新鲜(更新至2025-09-30)
披荆斩棘2025(更新至2025-10-02)
巴黎合伙人(更新至2025-10-10)
背后(更新至2025-10-05)
我家那闺女2025(更新至2025-10-07)
花儿与少年第七季(更新至2025-10-06)
甜蜜的任务(2025)(更新至2025-10-05)
你就宠ta吧(更新至2025-09-29)
假期中的她们(更新至2025-10-03)
乱“室”英雄(更新至2025-10-08)
向往的生活-戏如人生(更新至2025-10-04)
初入职场·中医季(更新至2025-10-06)
快乐趣吹风(更新至2025-09-26)
海角88号(更新至2025-10-06)
密室大逃脱第七季(更新至2025-09-23)